- UID
- 732
- 积分
- 5131
- 威望
- 576
- 桐币
- 1790
- 激情
- 3931
- 金币
- 0
- 在线时间
- 593 小时
- 注册时间
- 2008-10-22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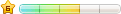
桐网贡士
 
- 积分
- 5131

 鲜花( 0)  鸡蛋( 0)
|
读帕慕克的《伊斯坦布尔》,被他的“呼愁”感动。“呼愁”,土耳其语“忧伤”的意思。这汉语翻译得真好,比忧伤更加的忧伤,且多了一层历史的悠长感。在帕慕克眼里,这种呼愁“不是某个孤独之人的忧伤,而是数百万人共有的阴暗情绪”。准确说,这是整座废墟之都的忧伤,覆盖在整个斜阳帝国一切残留之物上的忧伤。当帕慕克穿行在那破败、灰暗、没落而又处处遗留着古老帝国残砖断瓦的街头巷尾,他慨叹道:“我出生的城市在它两千年的历史中从不曾如此贫穷、破败、孤立。它对我而言一直是个废墟之城,充满帝国斜阳的忧伤。我一生不是对抗这种忧伤,就是(跟每个伊斯坦布尔人一样)让它成为自己的忧伤。”在帕慕克的笔下,整个帝国的残留物汇入他个人的生命里,渗入他的血液和生命,成为他个人的命运。
每一个历史时代的变迁,每一场大的社会运动的终结,以及一切庞然大物的轰然倒掉,都会留下一堆历史废墟,供人凭吊、回忆,让人忧伤不已。克里米亚战争瓦解了伟大的奥斯曼帝国,使帕慕克的伊斯坦布尔成为单调、灰暗的“呼愁”之城。“泥泞的公园,荒凉的空地,电线杆以及贴在广场和水泥怪物墙上的广告牌,这座城市就像我的灵魂,很快地成为一个空洞,非常空洞的地方。”
相对于帕慕克那座伟大的城,我的“呼愁”则来自一个带着集体主义余温的贫瘠村庄。我记得在我的童年,人民公社尚未散伙,生产队最大的产业是一座牛棚,黄牛、马、骡子和拉磨的驴杂居一处。那时候,公社的拖拉机站已经废弃,巨大锈红的铁疙瘩躺在黄叶枯草间;一座被鸟巢占据的烟囱早已不冒烟,围墙倒塌,废料遍地,那是乡村惟一的工厂……那时候,最爱闻的是汽油味,穿绿衣的邮递员骑着一个小电驴……最爱玩的是火和水,冬天玩火,夏天玩水;那时候,家里惟一的工业品是一个汽水瓶子,最好的玩伴是一只黑狗,我把它训练成了全村最凶猛的狗……我记得有一年,村里的苹果园一夜之间被铲平,每家分到了两棵果树,移栽在自家的院子里。但那些果树实在太老了,最终没有一棵种活。就这样,一片曾经开满鲜花的果园消失了,这既是集体时代最终散伙的象征,也是一个时代断层的标记。
后来外出读书,离开家乡二十年,我对家乡的很多记忆还停留在上一个断层里。最近几年再回乡下,发现一种新的“呼愁”出现了——村庄变得大而无当,崭新的民居和废墟杂陈,工业景观与田园风光怪异地并置在一起;河流变黑了,几乎再也找不到一条清澈的小溪;鸟巢变少了,那些长着美丽羽毛的鸟儿再也难得一见……还有,村中嬉戏的孩子,路上追逐的少女,天空中盘旋的鹰,以及河里游动的鱼,都到哪里去了?都消失了,故乡变得如此陌生。“就算是给鱼和鸟都打上一针/也已经救不回故乡的山河”(俞心樵诗句)。
也许只是因为“怀乡病”在作祟,才使我对过去的一切充满感念,而对眼下的现实感到不适?怀旧者总是对往昔的细枝末节充满偏执的记忆,只有还乡才能治愈这恼人的乡愁。而如今,乡愁越来越难以治愈,一遍遍的还乡却只能加重病情,因为故乡早已不是那个故乡。
当传统遇上工业化,后现代遇上集体主义的尾巴,乡村现实的种种乱象和未来的种种愁绪,似乎注定不可避免。如今,村里的年轻人已越来越少,他们大多成了新时代的游子,故乡只是他们的一个怀旧之地,“返乡”变得可望不可即。仍然生活在乡村的人们,他们幸福吗?他们还有未来吗?如今,村里的不少老人又开始怀念他们自己的往昔——那充满乌托邦情结的集体主义年代。至少那时候看病看得起,上学上得起,肉可以放心吃,那时候老鼠还是怕猫的,人还是有良心的……那时候,人们尚有一个“现代化”的未来新世界可以憧憬,如今的梦想又在哪里?我们如何重建自己的乡村世界?“新农村建设”,不是一个“新”字就可以解决的。
帕慕克尚有“如丝巾般闪烁微光的博斯普鲁斯”可以守望,而我们却依然处在自己长长的“呼愁”里
作者: 朵渔 2010-12-30 11:53:35 |
|