- UID
- 25094
- 积分
- 346
- 威望
- 4724
- 桐币
- 1205
- 激情
- 54
- 金币
- 0
- 在线时间
- 54 小时
- 注册时间
- 2007-11-7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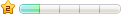
文都秀才

- 积分
- 346

 鲜花( 1)  鸡蛋( 0)
|
苍茫:回望与融入
——毕亮诗歌印象
文\洪放
诗人总是行走的,区别在于行走的方式不同。有些诗人,一生停留在故乡,但是他的灵魂在行走。而有些诗人,命定了他将远离故土,在另一种文化与风俗中生活和生存。不论是怎样的行走,都是借着行走的力量,深入到更广大的自然、文化与生命的律动之中。也唯其行走,才能成全诗人心中的爱与深层的神性,以及赤子般的纯洁与洗礼。
青年诗人毕亮就是。
毕亮显然属于我所提到的后一类诗人。十几岁时,他从江淮之间,来到遥远的新疆。应该说,故土对于他,也不可能是太深的烙印。而且,我曾经猜想:如果毕亮一直生活在他的故乡——这个曾经以文章甲天下而著名的桐城,那么,他也许会忽视和淡忘了故乡的许多风物,而将他诗歌的触角,伸向了故乡之外。而现在,他离开了。他生活在遥远的伊犁。因此,对故乡的另一种认知,和对异乡的拒绝与融入,让毕亮诗歌完全呈现了一种新的生动的气象。他是内敛的,又是激情的;他是忧伤的,又是苍茫的;他是独立的,又是共同的。
在《一个地方》中,诗人吟诵道:
同一个姓氏相继出生和死亡
一个我,曾经去过,却又离开了
一个诗人的一生,相对于土地的永恒,那只能是“曾经去过,却又离开了”。离开是一种成长,也是一种心灵的蝉蜕。我注意到:毕亮在大学毕业进入伊犁后,诗歌创作明显地出现了一个断层。在此之前,他更多的是对青春的吟唱、情爱的想往和对家乡的歌谣式的眷恋。在他自已早期印刷的诗集中,表象上的抒情占据了主要。然而,到达伊犁后,与边疆不同民族的深入接触和对他们往事与未来的不断了解,促成了毕亮诗歌的质的变化。早期的抒情,开始走向沉缓。意向上,也不再单纯,而是开始驳杂和荒芜。
《家谱》,是一首有典型意义的诗歌。我以为,它正是毕亮诗歌创作转变的一个例证。这首诗,一改以往反复使用的一些意象,而是选择了时间、纸张、表述等等意向,而这些意向都无一例外地指向了家谱所能带给诗人的感受:
家谱,一个丢失的词语,想打捞而无处着手
家乡成为故乡,事实上只在一念之间。家谱因此成了血液,成了牵系。毕亮对家乡桐城的怀念,更多的是对文化的怀念与景仰。走得越远,注定了对故乡文化的理解就越接近真实。在《桐城》中,他用简约的甚至如宋人白描式的手法,在回望中,抚摸过柳树、桐树和一册山河。这些意向之间的关联,已经不仅仅是诗歌的技术,而更多的是诗人自身情感的粹火与煅接。
去年,在伊犁的特克斯,我第一次与年轻的诗人毕亮相遇。喝酒,谈诗,当然更多地是谈到我们共同的家乡。在对诗歌的理解上,毕亮表现了惊人的悟性与自觉。我们谈到作为一个内地诗人,深入新疆文化后所应持有的立场与诗歌的面貌。这之后,我发现毕亮诗歌的断层出现了。他几乎是在很短的时间内,与过去的诗歌进行了告别。他开始行走在伊犁大地上,与不同民族的文化、信仰、过往相遇。他倾听他们,尊敬他们,亲近他们,并进而用诗歌和文化随笔两种方式,来进行抒写。《莫乎尔:葡萄的庄园》就是这样一首十分成功的诗作。它不是单纯地从文化写文化,从民俗写民俗,而是以一个游者的眼光,搜寻着莫乎尔这座葡萄的庄园的兴衰与沧桑。《磨河古城》中,诗人写道:
这是在磨河古城
贫困、饥饿以及疾病,某些人有生之年
忍受病痛的时候,看着城垣坍塌
摔碎了的磨刀石、炼铁打造刀剑的火炉
沉沉睡在黎明的护城河
这是直指历史的叩问,也是一个年轻诗人,在面对坍塌和消逝时,所能抒发的最动人的挽歌。同样,还有《阿力麻里城》等其它一些诗作。而这里,我想特别提到的是《三道河》。
仅仅十行的短诗,犹如小小的民谣,但是,却产生了无限的幽远与宁静。
一道河流过,牛羊成群,牲畜兴旺
两道河流过,树木成林,水草丰盛
三道河流过,村庄五谷丰登。
一唱三叹,仿佛民间歌手,在夜晚月光下的独白。而接着,诗人写道:
一个有着三条河的村庄
雨水的天空不曾熄灭,炊烟高高挂着
果实都埋在河底
父亲的梯田以及晚归的姻缘是三道河的黄昏
在这里,三道河的实象所指,已经完全虚化了。它可能是家乡,也可能是伊犁。它可能是梦境,也可能是现实;它更多的是诗人在对边疆文化的阅读中,所一点点努力构建起来的理想国。
[ 本帖最后由 毕梓桐 于 2009-6-22 22:56 编辑 ] |
|